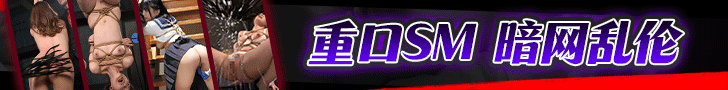“怎么?”
“我那后面路窄,蛮王一探便知后园无人踏足;你刚说在他那里不通房事要遭人耻笑,我后门不通给他知道了,岂不是叫他看我不起?”
“这……”
“是该想个法子开了它才好。”二皇子语中无邪,说得像要开个葫芦开个核桃;这话听在他兄长耳中,却是轰的一声。
“倒、倒也不必……”
长皇子回过神来,见二皇子跪在身旁,一手勾到背后去撬那暗道,他慌忙去抓弟弟的手想制住他,不当心手指擦过一瓣山竹瓤一样的白臀,指尖上凉软像点了水,心中却是火燎似的疼。
“皇兄,”男孩儿干脆赖倒在他怀里,攀着他的肩,“你可帮帮我……”
这怎么使得!长皇子心下焦急,手上却不肯推开这极美的男孩儿,任人摸进他怀里又是揉又是捻。二皇子贴上他,下巴搁在他肩上,一对软臀直往他手里送。
“当真的,我从了蛮王,你心不痛么?”
这一句话惊醒了储君。
他们蛮人不讲究吟风弄月,想必行那事也同逐猎、打仗一般,只图个痛快成事。看那些男妾个个剽悍结实,想也不需丈夫格外怜惜。蛮王这勇莽汉子,给他一个娇慵软嫩、未经人事的男孩子,他如何会哄?真像把上好瓷器托与卖艺人杂耍用,心要比瓷碎得快。
长皇子越想越恨。想着那英俊蛮人要如何剥开小皇子的衣袍,把个玉琢一样的人捞出来,按在兽皮褥子上采去花苞,也不管人怎么哭怎么叫,只管磨自己的兵器;小皇子渐渐哭不动了,下身也惯了,才觉出暗道中开了窍,被那蛮人的阳物顶着,越顶越有兴致,兴头上来顾不得庄重,夹着蛮王的东西大呼小叫、扭腰摆臀,再无大国皇族风范;待蛮王收兵出去,那羞人处精水和骚水混作一片,似风雨过新园,花落雨淖色犹鲜。
恨是恨……鲜也是真鲜。长皇子心上是哀痛,胯下是胀痛,竟也不知何时被二皇子解了裤子,一条孽根落在玉人素手中。二皇子低下身去,捧着那硬棒又吸又舔,烟花场里小官养汉不过如此。
“皇兄帮我……”二皇子牵着兄长的手往自己身后塞,“帮我开了这二十年的封,不要流落异国还被人取笑……”
是了。只为他在新夫面前挣点脸面,也为他新婚之夜少受苦楚……这背德事虽不该做,却是为着他好。长皇子想到这里,哪还忍得下火气,将他兄弟面朝下按住,握着湿漉漉的情柄就去推门。
他原想着是要费些工夫的,不料三推两推便进了一个枪头。长皇子虽情急,心智也未全昏,暗想道:这不像二十载未失之身。又一想:我怎能疑心弟弟清白,真不是人!心下骂了自己几句。
正想着,他弟弟在下面叫起来:“痛死了,痛死了,杀了我也没有这样痛的……”
果然还是新枝幼蕾!长皇子又对自己多骂了几句。
“你且忍忍,惯了就好。”他一手捞起纤腰,又嫌亵衣带子碍手,给他解了去,双手抱定白玉枕一样的腰身,不敢急进,浅尝慢送,款款而入。他这里不急,那秘径倒像蛇口贪食,吸着他拢着他,处处惹火,直惹得他不耐勾挑,一路冲杀。
如此弄了一时,二皇子不再叫疼,哼哼哀哀有些媚态了。
长皇子问他:“可好受些?”
“不似先前难捱了。”
又问:“可有趣味了?”
“羞人答答的,不好说。”
长皇子差点要说“这时知道羞了,方才自掰屁股的是哪个”,又一想,弟弟性本贞纯,都是为着和亲顺利、两国太平,是大忠大义之举,自己不体谅他忍辱负重,还想寻他开心,真不是人!
“不说也好。我自己看来。”
长皇子暂收兵戈,将二皇子翻身过来,才见花容红透,眼含烟雨,美不可言。提刀再入,愈发顺滑;二皇子双手攀住长兄脖颈,兰息纷乱,媚叫不绝。得趣与否自不必问,万般快意都在一张俏脸上。
又一时,二皇子抬手拭额,擩了一把香汗,楚楚道:“我耐不得了……”再看股间,玉茎娇软,皇亲国戚在腹上流了一片。
见他丢了,长皇子不敢再多劳累他,忙说,“你夹紧些,我丢在里面。”二皇子依言奉承,举身相迎,园门一拢,甘露尽入囊中。
兄弟两个少歇片刻,长皇子起来拿了帕子,将弟身上沾污处细细拭遍,又替他系了小衣。
“好哥哥,你可知道……”
“知道什么?”
“算了,不提。”
二皇子酥手抚过兄长面庞,又歪在他怀里。
“等到了蛮国,你不要走了,我们一同降了那蛮王!”
长皇子听了一激灵,“胡说什么?!”
“蛮王和我素未谋面,谈不上情分,我不过是去做个使者。你降了他,哪还用得着我。”二皇子脸上红扑扑的,也不知是余韵未退还是新潮又起,“到时候请他指婚,给我们两个配成一对儿……”
蛮国没有,指婚,这说法,最多请蛮王为他们做个证婚人……呸,呸,想什么呢?!长皇子暗骂自己因色失智,被弟弟胡说拐走了心思。
“我不怕做活,也不要人伺候,只要和皇兄一生厮守,像他们蛮人一样打猎、耕种、牧马放羊,天黑了就在帐房里……行好事。这样的日子,皇兄你不想吗?”
“……不早了,快歇息吧。” 长皇子说着,把他兄弟按进被里,“胡话不许再说,叫人听见哪还得了。”
“皇兄……”二皇子还不肯罢, “你亲我一个再走。”
长皇子犹豫再三,还是低头在那樱唇上碰了一下。二皇子扯住他的衣袖,硬是将一个吻弄成两个。
“皇兄,你就依了我……”
长皇子狠下心拂开他的手,“再议,再议……”
他系好衣裤,心虚得头也抬不起,昏沉沉地出了帐房。
【完】